学党史|红军在德江铁纪慰民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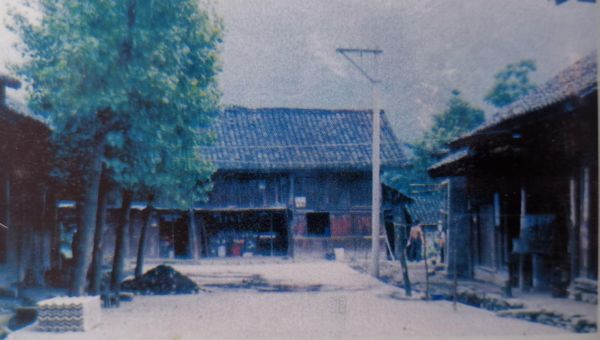
图为红军在德江黄家堡时的指挥部旧址
党风廉政建设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工作内容,即便在革命战争年代也是如此。
1934年7月,贺龙等率领红三军在黔东正式创建了云贵地区第一块革命根据地——黔东革命根据地。
在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贺龙等领导人不仅领导根据地军民粉碎了外部敌人的武装进攻,而且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腐倡廉斗争,有力地反击了来自革命阵营内部各种腐化变质思想的侵蚀。
“红军不拿农民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交公”“损失(群众的财物)要赔偿”,是红三军在黔东时期铁的纪律。
1934年5月,红三军政治部颁布的《中国工农红军的任务和纪律》明确规定:“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坚决反对白军和土匪领袖焚烧房屋抢劫民众财物的办法。”
1934年8月,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处编印的《乡苏维埃》中规定:“对贪污腐化,侵吞和滥用公款的人员要进行纪律和法律的制裁。”
《革命委员会政治纲领及组织法草案》中规定:“不准抢掠工人农民财产,如犯者处死刑;不准侵吞公款,犯者重罪……”
红三军进驻时的黔东,由于生产力极其低下,基本属于自给自足、封闭式的自然经济状态,再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使黔东军民遭受到巨大的经济困难,在这样的环境下,领导的率先垂范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由于当时条件困难,根据地一切都要从节俭出发,开支控制很严。从战士到军长,凡需开支都要通过经理处批准,个人不能任意提高标准。打下沿河县城后,贺龙的警卫员为方便首长夜间行动,提出领两对电池,保管人员只认批条不认人,硬是等经理处批条到手后才发了货。
当时会议记录本、军部首长的工作笔记本,也是正面写了又写背面(当时用本地草纸,一般只能写一面)。召开会议时,为节约灯油,常常只在记录员面前点一盏灯。
在党员干部的率先垂范下,黔东根据地的军民、官兵以罕见的吃苦精神,共同渡过了根据地最艰苦的建设时期。
黔东根据地在开展财经建设的同时,制定了各种规章制度和纪律,即:上级要根据财经的实际状况给予指示;各单位每月要有预算和决算报告上级,上级要下达下月的财政预算;各级要经常把粮食、油、盐、衣服等物资统计报告上级;坚决执行现金集中,统一收归监护大队管理的规定。
老红军贺文玳回忆:部队和游击队把打土豪和战争缴获来的东西,都交经理处或没收委员会统一保管、记账。管钱、管物各是一批人。动用司令部经理处的钱物,必须要搞预算、决算,经首长批准,再凭领取单位的领导人打领条发钱物。经理处只起个保管的作用。各级财经机关都有结算账簿和收支账。如果账、物不符,就要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对于各部队私设“小金库”问题,贺龙派时任红三军经理处监察委员会委员的孟子厚和贺文玳到各师去查。结果发现各师除了经理处发给的钱外,还把接受各商会的捐款,打土豪没收的钱款都作小金库没有上交。
黔东独立师贺炳炎师部就搞了两个账本。监委会将调查情况向贺龙汇报后,贺龙亲自找贺炳炎谈话,贺炳炎只好老老实实的全部上交。其他师、团见贺龙这样认真,就把私藏的钱全部交了出来。
廉政建设不仅仅在军队建设、财经建设,同时也体现在日常生活中。
贺龙经常是穿一身青土布对襟衣,一双草鞋,完全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打扮。关向应也一样朴素,他几年没有被子,临睡时就铺些茅草,一条破军毯既作披衣又是被子。乍一见难以分清谁是领导谁是战士和农民。
为严肃纪律,红三军以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翻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惩罪办法》作为教育和规范党员、红军官兵和苏维埃干部的革命纪律的重要内容之一。
如唐家溪苏维埃文书李金忠,作风恶劣,品质败坏,生活腐化,他利用职权记假账,从中贪污大洋7元,经苏维埃代表大会讨论撤职后交保卫局判处死刑。还有南腰界游击队队员秦登仲在打土豪时藏匿财产,进行贪污,也被保卫局处以极刑。
为解决军队经费,部队经常到周边地区打给养,并要求打给养所得必须全部上交,任何个人不得私藏。如在德江县毛岭有一个战士私自出售打给养所得的一床被条,隐瞒大洋一块,发觉后被处以极刑。
红军在德江建立黔东革命根据地时坚守铁的纪律的作风,坚持为民谋利的方向,无不体现着共产党人廉洁奉公精神。(德江县纪委监委)
